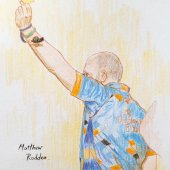《六十二》|深海郵箱
《六十二》|深海郵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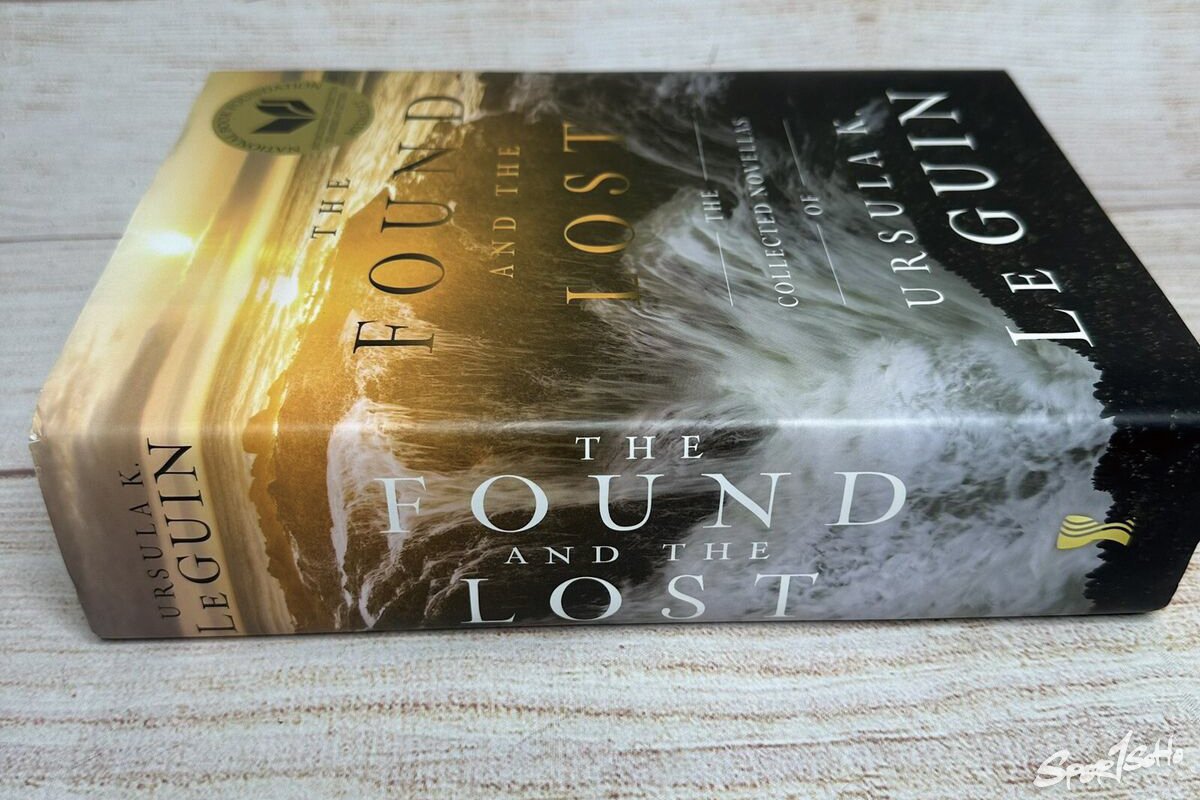
上次說到迎接七月的畢業禮,我對這場儀式的一份憧憬,源自於它所盛載的經歷和體會。
當初選擇修讀英國文學,除了閱讀英語文學作品是自己興趣,也是考慮到想當全職運動員,希望選擇一項自己較有把握的主修科,而且即使中間停學也不用很吃力追進度的科目。間間斷斷的停學,大學已由三年學制改成四年,學習模式亦由紙張和白板變成ipad和zoom的年代,大部份課程連實體書本都不用買,某些課程更以線上學習為噱頭。
大學第一個學期報上的課堂都特別有趣,可能因為是授堂模式的衝擊 —— 即使教授以傳統演講模式授課,但她的演繹一點也不傳統,每張幻燈片上只有大大的幾隻字體,她兩小時的演講卻能
凝聚學生的專注力和互動。課程內容的廣泛性都讓我十分深刻。
中學時接觸的英國文學多數是一些傳統名著和基本理論,到大學主修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這一科也可以細分成不同溪流——我讀的不止是英國或者美國作家的文學作品,還有印度、加拿大、法國、日本和香港作家的英文作品,有時內容可能夾雜他們的母語,或者像莎士比亞那樣,有自己創作的一套詞匯。我本來就很喜歡小說,漸漸在大學又發現了詩詞。
我讀大學頭兩年還是十分崇尚十八至二十世紀初的英國主流作家和作品,最後兩年讓我大開眼界,愛上了一些教授們介紹的「side-cut」(不是香港主流會認識的,或者是我太井底),例如
Rachel Cusk,Ella Hickson,Italo Calvino,Jo Shapcott,當然還有些也是鼎鼎大名而我之前從未接觸而瞬間深愛的,例如Ursula LeGuin,Amitav Ghosh,Carol Ann Duffy,還有因為大學文學節而可以親耳聽到她朗讀和分享自己作品的Mary Jean Chan(上課時教授有安排身在英國的她為我們在Zoom上相見,沒想到疫情後能把她帶回香港!)。
不過讀文學當然有一些很地獄的經歷,尤其是那些令我敬佩但又頭痛的哲學家和他們的理論,留待下一期分享這些痛苦的畫面吧。
Text:陳晞文
Photo:作者提供
原文刊於《運動版圖》2025年7月號
更豐富內容請支持印刷版或電子版!